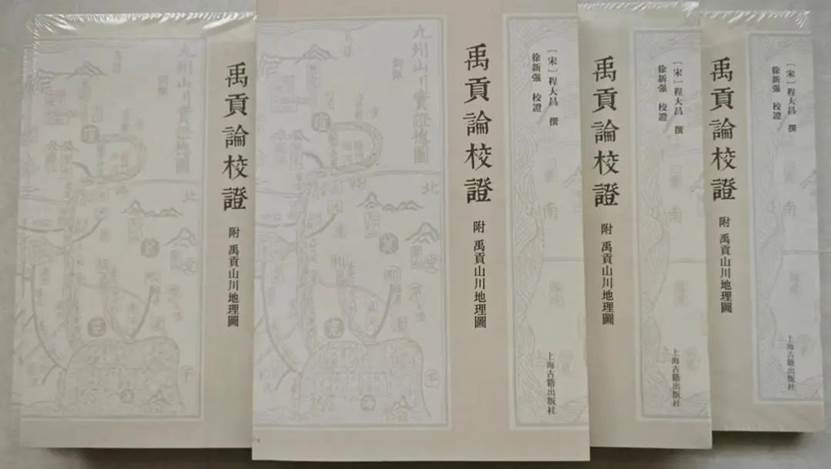
《禹贡论校证》(附禹贡山川地理图)
徐新强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年11月
作者簡介

徐新強,山東曲阜人,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尚書》學研究中心主任、曲阜師範大學“杏壇學者”,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訪問學者,中國史儒家文獻博士。山東孔子學會理事、山東省傳統文化教育傳承研究會副秘書長,主要從事經學文獻整理及“禹貢圖”文獻研究。
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研究專項“禹貢圖集成與研究暨資料庫建設”1項、主持省部級專案2項,參與國家社科冷門絕學項目1項。獲得2018年山東省教學成果獎一等獎1項(參與)、2018年國家教學成果獎二等獎1項(參與),於核心期刊、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二十餘篇;專著《禹貢圖文獻集成(共十冊)》1部;《尚書文獻選輯(共六輯)》副主編等。
內容簡介
“《禹貢》圖”與《禹貢》學、歷史地理學密切相關,涉及河流疏導、水利興修、邊疆治理、民族分佈、政治經濟等眾多問題,“《禹貢》圖”研究不僅對完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有著積極意義,對發掘經典所蘊含華夏民族的原始記憶、實現鑒古知今也有著現實意義。但由於相關問題學界關注少、研究難度大而鮮有相關研究成果。由於時空遠隔,宋前“禹貢圖”皆已散佚,因此,對宋代“禹貢圖”文獻的整理與出版于“禹貢圖”研究有著重要的文獻價值。宋程大昌著有《禹貢論》《禹貢後論》《禹貢山川地理圖》,這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最早且最系統的“禹貢圖”文獻,其雖名為三編,但實為一體,三者文圖互為參照,故本書合而校證,對於研究宋代“禹貢圖”的源流有著重要意義。
本書以宋代程大昌著《禹貢論》(宋淳熙八年泉州州學刻本)為底本,包括《禹貢論》《禹貢後論》《禹貢圖》三個部分,是程大昌對宋前《禹貢》所載地理、地圖、貢賦、荒服等問題的考證,論前圖後,依其所論繪以“禹貢山川地理圖”。本書撰寫分兩個步驟,一是,對《禹貢論》《禹貢後論》《禹貢山川地理圖》進行點校,並以“四庫本”和“錢氏指海本”為參照進行對校,歧異處參核上下文、後世《禹貢》學文獻如明代《禹貢要注》、清代《禹貢錐指》等加以判斷取捨。二是,對《禹貢論》《禹貢後論》《禹貢山川地理圖》所論依篇目將歷代學者相關的考辨列於其後,歸納學者的主要觀點,並進行簡單的疏解;對原書中繪圖作簡單闡釋。對存在爭議問題,作者則考察諸觀點差異,利用史籍、地志、地理等文獻進行印證,採用訓詁學、地理學的方法進行校證,加以按語點評程大昌之論,提出作者自己的觀點,是為“校證”。歷代學者觀點紛歧而無定論者,則守古人闕疑之訓,只列出各類論說觀點,不予以結論。
通過對《禹貢論》點校、集釋、校證,不僅可以發現宋代《禹貢》學由傳統經學注疏向歷史地理學的轉向,由此也可以發現宋代於河流治理、疆域盈缩等方面的政治觀念。而通過元、明、清相關《禹貢》學著述的校對,亦可以發現宋至清,對於地理、疆域以至治政理念上的發展與變化脈絡。
目錄
前言
凡例
禹貢論
禹貢山川地理圖
參考文獻
前言
《禹貢》是《尚書·夏書》中的首篇,記載了“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的一系列故事,歷來被視為與地理、疆域、貢賦等國家治理相關的重要文獻。“禹貢圖”,也稱禹跡圖,不僅包括歷代《禹貢》學著述中所載大禹治水,依山川、導江河、分九州、理貢道的地理圖,還包括別貢賦、分夷夏、畫荒服的政治治理一類的圖。除了對擘畫九州的載錄外,“禹貢圖”與《禹貢》經文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早期的貢、賦有著密切的關係。通過對不同區域土壤的考察,綜合區域經濟狀況來確定賦稅的等級;通過對各州所出物產的考察,從而確認貢物的品類;通過對水道的疏通與溝連,不僅實現了治水避災以保民生的目的,也確保了貢賦運輸的暢通。
“禹貢圖”與《禹貢》經文互為注腳,使《禹貢》意涵的延展擺脫時空限制,借助“禹貢圖”可以清晰判斷九州山川河流的地理方位,由此也啟發了後世學者“左圖右書”的治學傳統與經解方法。
“禹貢圖”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兩個重要時期:一是“禹貢圖”的產生期,這一問題從古至今學界觀點分歧不一,關於“禹貢圖”產生,歷來有禹夏說、西周說、春秋說、戰國說、秦漢說,其時間跨度幾乎涉及了從上古至兩漢整個華夏文明的形成期。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先民都是以圖來記錄對自然的認識和改造,由此來說“禹貢圖”應該出現的很早,它不僅反映了早期先民對疆域、地理的認知,也是其朦朧的天下觀、一統觀的體現。二是“禹貢圖”發展的轉折期。傳世文獻中,宋前的“禹貢圖”皆已散佚不見,我們已無法看到唐及唐前“禹貢圖”的形制。宋時應該還有相當數量的“禹貢圖”流傳,這為宋代“禹貢圖”繁盛奠定了文獻基礎。從宋代“禹貢圖”文獻可以知道,宋人習承了唐甚至唐之前的“禹貢圖”並在其基礎上予以發展,使“禹貢圖”的繪製更完善。宋人對《禹貢》的認知也由經學轉至地理學的向度,宋人“禹貢圖”不僅是其經學、地學思想的載體,其中更是寄寓了宋人外憂內患下的家國觀念。因此說,宋代“禹貢圖”大量出現不僅在文獻層面上出現轉折,宋代“禹貢圖”被融入了士人的家國幽思,成為重要的思想載體,也出現了思想發展上的轉折。從這兩個角度來看,宋代在“禹貢圖”發展歷程中上承漢唐下啟明清,是“禹貢圖”史中的重要結點,在“禹貢圖”發展史上有著重要意義。
對“禹貢圖”出現的探討
“禹貢圖”與《禹貢》篇的形成,由現代考古發現來看,與中國早期貿易中的水道交通的發展關係密切。從文本上來看,《禹貢》託名于大禹,反映大禹治水之事及夏禹時期各地向冀州交納貢、賦的情形。但是從歷史的視角來觀照這一表述,則會發現這種表述失之於客觀。夏禹之時,華夏大地上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據傳世文獻所載可以知道,到殷商之時,以河洛為中心的區域內大小邦國約有二千,周初諸侯至少也有八百,而夏禹之世則必然不少於此數。《堯典》“協合萬邦”之說就反應了堯舜之時邦國林立的社會面貌。《老子》“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話,正是上古社會邦國並存的真實寫照。在這種邦國割據的社會現實下,各國不相往來、以鄰為壑,先民的意識十分的狹隘,所知道的也只是天下最小的一部分事情,更不要說虞夏之時。在萬國林立的夏禹時代,以《禹貢》所載之規模,以一人甚或一邦國之力實現天下九州的劃分、山川河流的疏導以及土壤的勘測分類,並不現實。而《禹貢》篇中所反映各州向冀州交納稅賦、特產的記載也不可靠。夏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在天下九州的範圍內,要求各地所出物產進貢至冀州一地或一國的可能性十分的小,但並不能因為這種矛盾就直接割斷“禹貢圖”與禹、與夏的內在關聯。從文明發展的一般規律可以判斷,圖的出現早於文字。結合考古發現的成果判斷,“禹貢圖”的出現也應早于《禹貢》經文。“禹貢圖”與《禹貢》所反映又為夏禹之事,二者的出現早至何時,無法確知,但可以確定的是,“禹貢圖”與《禹貢》表述的形成,是一個有先有後、逐步形成的過程,而其源頭極可能要早至夏禹治水之前。
上古之時,由於江河水道都處於自然狀態,無人力開掘或人為疏通而極易壅塞,在經歷降水或其他地質災害時,常常出現洪水氾濫的情形。因此,在一定的區域範圍之內,夏禹可能借鑒先前貿易交換過程中繪製的水道路線圖協調各鄰邦疏通水道,實現洩洪導水的目的。《周公職錄》曰:“黃帝受命,風後授圖,割地布九州”,是九州依圖而分。《水經注》曰:“禹理水,觀於河,見白麵長人,魚身,授禹河圖而還於淵。”這些都是禹依圖治水的文獻,而治水成功之後,大禹接受鄰邦物產作為饋謝之禮,在這個過程中,圖與文被禹或其下臣重新繪製與修正,而出現了“禹貢圖”及《禹貢》的雛形。從新出土的西周中期的遂公盨“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廼拜方設征”的銘文來看,西周時期,成熟的《禹貢》式的表述已經出現。西周之時,其統治雖並未實現完全的天下一統,但周天子封邦建國、分封諸侯,一定程度上成為天下共主,或出於水道疏導亦或政治治理的需要,在夏商已有的山川水道的圖文載錄基礎上,對山川、藪澤、河流、土田、貢賦等的梳理擴展至天下九州,並條分縷析繪之為圖,記之為文,形成了反映西周時期山川地理物產的圖錄。周人尊夏,因而託名于禹而稱之為“禹貢圖”與《禹貢》。這是其初有天下,亟須明晰疆域、掌握天下山川形勝,劃分區域、征繳貢賦所必需的工作。而“禹貢圖”不能詳盡展示的內容則輔以文字說明,也就有了《禹貢》式的表述。周人對夏禹之時出現的“禹貢圖”及《禹貢》式表述的承襲與發展,不僅是周初統治者國家治理的必然,更符合其尋求統治合理性以及尊夏的心理要求。
通過考古發現可以知道,在距今大約4000年前後的龍山文化時期,時間上與文獻中所記載的禹夏有交集。這一時期的貿易交換已經十分的發達,貿易交換成為社會活動中的重要內容,貿易交換的範圍也已十分的廣泛,涉及物品種類繁多,在當時主要包括農業、漁獵、採集的農副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甚至還包括開採的稀有礦產品。龍山文化時期貿易交換已經形成不同層級的市場體系,這一體系按照規模由小到大又分為初級集市、區域市場、跨區域市場三個層次。不同層次的市場交換的物品也不盡相同,由於跨區域市場面對的需求更廣、更複雜,因而還出現了專門從事貿易活動的商人。跨區域市場形成了一個獨立的貿易交換體系,以調節大區域範圍內物產供給。由於運輸距離比較遠,在這一過程中又出現了長途運輸的通道和沿途的節點性市鎮,以及便於長途運輸的具有較大增值空間的商品。這些具有較大增值空間的商品多為經過人力再加工的手工業產品,包括陶器、石器、玉器等。龍山文化時期的陶器生產十分的發達,產量大器型多,這與當時陶器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以及生產力水準的提升密切相關。石器的生產在這一時期並未象陶器一樣形成規模,從考古發現來看,聚落遺址上的石器成品和使用損壞的石器比較少。由此,考古人員推測,石器產品不主要是供給本聚落使用,大多則是作為商品交換出去。而玉器以及一些精細石製品是當時的高端產品,一般出現在大型的中心聚落或是祭祀遺跡中,一些比較精美的石器和小件玉器也在少數墓葬中被發現,屬於專供上層消費的奢侈品。精美石器與玉器的製作,人力、物力投入相對較大而產量卻較小,成本高昂,只有掌握大量公共資源的統治階層才有可能擁有。(孫波《山東龍山文化的聚落與社會》2019)因此,這些高附加值的高端產品的享用也成為上層統治者特權與地位的象徵,這類奢侈品自然成為跨區域貿易交換的主要內容。
這一時期,跨區域的市場交換已經發展成一個成熟的貿易體系,其所交換的物件正是包含一定技術和勞動含量且具有較高增值空間的高端產品,由於跨區域貿易交換的複雜與交通運輸路線的原因,已經出現了能夠識記交通路線,懂得貿易交換規律的專業商人,追求高端奢侈品的貴族統治者。對奢侈品的追求以及專業化商人的出現使龍山文化時期貴族手工業及跨區域的交流網路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統治集團中的上層貴族則通過其所掌控的權力攫取財富,進而強化其身份,享受奢華的生活。考古發現,龍山文化時期高等級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石器、玉器表明了手工業的發展和上層貴族對外交流的擴展。以石器、玉器生產和流通為代表的手工業被納入上層統治者的控制之中,這也是社會複雜化深入發展的結果。早期社會複雜化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人類社會群體內出現了制度化的不平等,居於統治或支配地位的貴族往往以貴重、罕見或外來的奢侈品,以及精緻考究的居址、墓葬等物化的形式來表現、強化其身份和地位。(戴向明《中原地區龍山時代社會複雜化的進程》2012)在出土的山西陶寺城址中期王級大墓中就發現了來自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和紅山文化的器物,而夏禹之時,統治者對稀有、貴重物品的追求,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跨區域貿易和水陸交通的發展。
龍山文化早期,各邦國跨區域貿易交換已經出現。到了《禹貢》記載所反映的龍山文化中晚期,跨區域貿易交換模式已經十分的成熟,在貴族統治者的墓葬中,具有身份象徵意義的外地域特產已經十分的常見。《禹貢》經文中所載作為貢、賦通過跨區域水道交通運送至冀州的各地物產,最初可能並不是以貢、賦形式得來,而恰恰是通過這種早期的遠端貿易交換獲得。從根本上來講,貢、賦除了包含有上下級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外,本身與交換流通也有著緊密的聯繫。《說文解字》釋“貢”“賦”皆從“貝”,段玉裁釋“貝”:“謂以其介為貨也”,釋“賦”:“經傳中凡言以物班布於人曰賦。”由“貢”“賦”二字本意來看,其與物產的班布流通有著一定的聯繫。上古時期的貴族統治者,或是對其他邦國文化不甚瞭解,或出於鞏固自身統治威信的需要,將貿易交換得來之物喚作外邦之貢、賦。為滿足上層貴族統治以及奢侈生活對此類“貢”“賦”的需求,貴族統治者積極推動跨區域的遠端貿易交換。出於城邦間跨區域貿易交換的需要,專門從事跨區域貿易交換的機構或人在進行遠距離貿易的過程中,便會探索水陸交通的輾轉路線,為幫助記憶或方便後人對交通路線的掌握便繪之成圖。早期人類社會的交通運輸並不發達,沒有人為開通修建的交通途徑,跨區域間的交通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自然形成的水道交通網絡,因此他們所繪製的交通路線圖在實質上便是水道交通圖。龍山文化時代還沒有通行或成熟的文字,所以先民們便將水道交通路線用圖畫的形式記錄下來,而“先民最初的地理知識是用圖畫來傳達的”,這種圖示的水道交通圖或許正是“禹貢圖”的渺遠前身,跨區域貿易的水道交通路線圖也為夏禹之時洪水治理、隨山刊木、水道疏浚提供了借鑒與指引。
在洪水治理的過程中,夏禹不僅開掘疏通水道,而且還以大山丘原為標識,修正並完善早期貿易交換過程中所繪水道交通圖。此時的水道圖還局限於以堯、舜、禹所掌邦國為中心的鄰近城邦範圍內,遠沒達到天下九州的廣袤地域。直到西周之世,發源于西方的周人疆域橫跨東西而奄有四海,西周以天下共主的姿態,託名于大禹而最終形成“禹貢圖”與《禹貢》經文。“禹貢圖”與成熟的《禹貢》經文形成的西周時期,去古未遠,有一定的史實為依託,因此也可以支撐“禹貢圖”與《禹貢》早出的觀點。歷史時期,在地理上,陵穀有升沉、土石有消長、河流有變遷,歷代為政者和學者在早期圖、文的基礎上不斷繪製、修正並完善所處時代的“禹貢圖”和《禹貢》經文,突顯出其經學、歷史、地理以及治政等領域的重要價值。“禹貢圖”和《禹貢》經文不僅客觀的反映了九州地理劃分,也是中國天下九州一統觀念的肇始,作為地理與治政的重要文獻被歷代學者反復解讀。
宋代“禹貢圖”發展概況
傳世的宋代“禹貢圖”著術按其作者先後及成書時間,首先有舊題為蘇軾撰《歷代地理指掌圖》,但《四庫提要》以之為後人託名蘇軾而實為北宋稅安禮所撰。《歷代地理指掌圖》共有圖四十四幅,始自帝嚳九州至宋州郡,繪製了歷朝歷代的疆域圖,圖後均附說明。而其中“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禹跡圖”與《禹貢》經文所述“禹貢圖”更為近似。而“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中所繪海岸線、河流、長城等的輪廓,與宋紹興七年石刻《華夷圖》很相似,尤其是第一幅圖後附的圖說與《華夷圖》上所刻文字說明十分一致,由此也可以看出宋代“禹貢圖”與唐代“禹貢圖”源淵關係。
北宋楊甲《六經圖考》大致成書於紹興中期,楊甲以圖譜的形式展示“六經”所關涉問題,其中《尚書軌範撮要圖》包括“隨山浚川圖”“九州疆界圖”“治水先後圖”“九州九山名數圖”“五服圖”等。與之前的石刻《禹跡圖》、《地理指掌圖》相對照,宋早期的圖多於宏觀總圖的繪製,其反映的是對整個朝代對疆域、區劃的關注,可能更多的是體現了宋人天下統一的思想觀念。而楊甲之圖除了總圖之外,更增多了導山、治水、五服之圖。由此,可以發現,此時宋人已經不單純的將“禹貢圖”作為一種思想與觀念的代表,而逐漸的向山水疏導實踐變化,顯現出地理學上的特徵。
南宋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主要包括山川大河、貢道碣石等圖三十幅。淳熙四年,程大昌侍經筵而講《尚書》,考證《禹貢》篇山川實地則事為之圖,即《禹貢山川地理圖》,因此其圖繪於淳熙四年前後。其《序》說:“稽求先儒舊說,各以其語先為之圖,從而辨證其誤。舊說既竟,乃出愚見別為圖以綴其後。” 他先歸納前人舊說繪圖,而後考辨其正誤,再依據新解繪圖於後,通過新舊對比,考察圖示及論說。程大昌繪圖理論與方法比晉、唐“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更進一步,其所繪各圖不僅明確標示東南西北方向,並且“圖以色別,青為水,黃為河,紅為古今州道、郡縣疆界,其用雌黃為識者,則舊說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 對不同稱名的山水、河流、郡縣等都採用不同的顏色區別展示,一般水道用青色,黃河則繪以黃色,古今疆界用紅色,而不能確定的舊說則用雌黃表示。四種不同的顏色共繪於一圖,將不同的地理形態鮮明地區分,而這種多色繪圖的方法與理論,與宋代社會經濟、文明的進步密不可分。而相較於之前的“禹貢圖”,程大昌之圖更注重考察《禹貢》山川、河流的歷史變遷,而具有了顯著歷史地理學特徵。因此,本書亦以程大昌《禹貢論》《禹貢後論》《禹貢山川地理圖》合而為一,點校並按以集說,以期求證於文獻。
宋代著述中“禹貢圖”相對較多,除此外,還有一些圖解“六經”、圖解《尚書·禹貢》篇以及注解《禹貢》的專書中也零星的繪製了“禹貢圖”,其圖幅相對較少,或三五幅或一二幅。如,略晚于程大昌的唐仲友繪製的《帝王經世圖譜》,以圖譜梳理“六經”旨要,其中的“禹貢圖”包括“禹跡九州之圖”“禹貢九州山川之圖”二幅。唐仲友不僅以圖展示九州山川疆界,還以繪有“禹貢九州譜”,以“譜表”的形式統計九州的山、川、澤、原,還將各州邊界、物產及少數民族居民予以統計。再稍晚的傅寅繪有《禹貢集解》,《永樂大典》載其書則名為《禹貢說斷》。傅寅曾著有《群書百考》,考辨群書輔之以圖,《禹貢》之圖說概為此書中一種。因當時解說《禹貢》諸家對九河、三江、黑水等考證結論歧出,傅寅條列諸說而斷以己意,並繪製“禹貢山川總會之圖”“九河圖”“九江圖”“三江圖”共四幅。還有託名鄭樵的《六經奧論·書經》,其中考論《禹貢》篇時繪有《禹貢九州之圖》一幅。《六經奧論》中論《書》一條引用《朱子語錄》的話,並稱朱熹諡號,則可判定此書必不為早于朱熹的鄭樵所作,應該成於南宋末。
結合文獻的間接記載來看,宋代“禹貢圖”遠不止這些。南宋陳振孫著《直齋書錄解題》記有《六合掌運圖》:“凡為四十四圖,首列禹跡,次為中興後南北二境。” 其前兩幅圖與“禹貢圖”相關且以“禹跡”領銜,有統攝九州六合之意。清胡渭《禹貢錐指》中《禹貢圖》的前序中也說:“合沙鄭氏東卿著《尚書》圖七十有七,其系《禹貢》者凡二十五。” 可見鄭東卿也曾繪有“禹貢圖”。另朱彝尊《經義考》載錄黃千能《禹貢圖說》、孟先《禹貢治水圖》、張性善《禹貢沒革圖》、王柏《禹貢圖》等皆繪有“禹貢圖”,但由於時空的遠隔,這些圖籍皆已散佚不可見,其中所繪“禹貢圖”雖不知其詳,但根據已有之圖推測,有宋一代“禹貢圖”除名物的差異外,應該相去不遠。直接及間接可知的“禹貢圖”之外,概還有不可勝數的“禹貢圖”湮沒於文獻傳承的歷程之中。傳世的宋代“禹貢圖”不僅數量上遠超之前,在圖的分類上也比宋前要多。宋代不僅有宏觀的“九州圖”“沿革圖”,還有具體展現導山、導水、貢道、甚至五服的專圖以及各類指掌圖和對地理、物產等名物梳理的圖譜。而在圖的繪製上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由朱墨區別古今疆域沿革發展至用不同的顏色區別不同地理特徵和地形地貌。此外,宋圖也開始標示東南西北方向用以確切指示地理方位。但宋代“禹貢圖”除石刻《禹跡圖》全圖繪有方格並注明比例尺外,其它宋圖皆無繪製方格與比例尺以辨廣輪之度。晉裴秀已有“分率”之論、唐賈耽亦有繪有方格體現分率的《海內華夷圖》,由傳世宋代“禹貢圖”來看,宋圖還僅僅是指示性作用,並沒用於具體地理位置及相對地理距離遠近的考定,更多是一種思想觀念上的載體。
宋代“禹貢圖”的無論是於規模還是繪圖水準都有了巨大進步,這不僅與社會的進步有關,還與宋代對“禹貢圖”的重視與傳習有著密切關係。宋代對於“禹貢圖”的研究與傳習已經成為士人學子修學的重要內容。潘晟《宋代地理學的觀念、體系與知識興趣》中引宋代劉敞《觀林洪范禹貢山川圖》“於今傳者為張宜”一句推斷:“北宋時繪製《禹貢山川圖》可能在某一範圍內形成了師徒相授的傳統。” 如果這一推斷成立,那麼至少在北宋時期的學術領域或官方行政範圍內對“禹貢圖”已經十分的重視,並在一定範圍內得以習承。西安“禹貢圖”刻石寫有“岐學上石”,有學者考證說是當時西安府學獲此圖,為教授學生而刻于石上。同樣,鎮江石刻則更是明確說明為鎮江府學立石。而辛德勇考證山西石刻“禹貢圖”最初立于縣東南的稷山縣學。我國歷來有將經典刻之于石以為標準用以傳習。由此三地府學所立“禹貢圖”刻石來看,宋代確有“禹貢圖”的研究、傳授及繪製,並且將此“禹貢圖”視作經典刻石以供傳習。宋代已經將其做為一門學問在官學被傳授,自然宋代“禹貢圖”的數量、類型與規模遠比今天所知道的更多,而宋人對其繪製與闡述還會有不同的側重,承載著不同學派的學術特徵與思想觀點。
程大昌著《禹貢論》《禹貢後論》《禹貢山川地理圖》雖名為三編,但實為一體,三者文圖互為參照,故合而校證。《禹貢論》《禹貢後論》《禹貢山川地理圖》存世版本主要有北京圖書館藏宋淳熙八年泉州州學刻本、淸康熙成德刻通志堂經解本、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道光間錢熙祚守山閣刊《指海》本等。通志堂經解本,以今已散佚的天一閣鈔本為底本,但該鈔本有“論”無“圖”,且“敘說”不全。四庫全書本以今已散佚的《永樂大典》本為底本,但仍闕《九州山川實證總圖》《今定禹河漢河對出圖》二圖。《指海》本可認為以《四庫》本為底本。其餘如《清芬堂叢書》本則有“論”無“圖”,而《四庫全書薈要》本則有“圖”無“論”。因此,依據版本流傳的情形,本書校證以宋淳熙八年泉州州學刻本為底本,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對校。
本書為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研究課題“《禹貢》圖”集成與研究暨資料庫建設”的文獻整理的部分內容,因此作為課題組成員的兩名研究生趙茜茜、王建兩名研究生在文獻搜集整理過程中做了大量工作。限於作者及課題組成員的學術積累及研究水準,在點校及校證闡釋過程中,肯定還存在大量的錯誤和疏漏之處,請前輩批評指導並謹以此就教於大方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