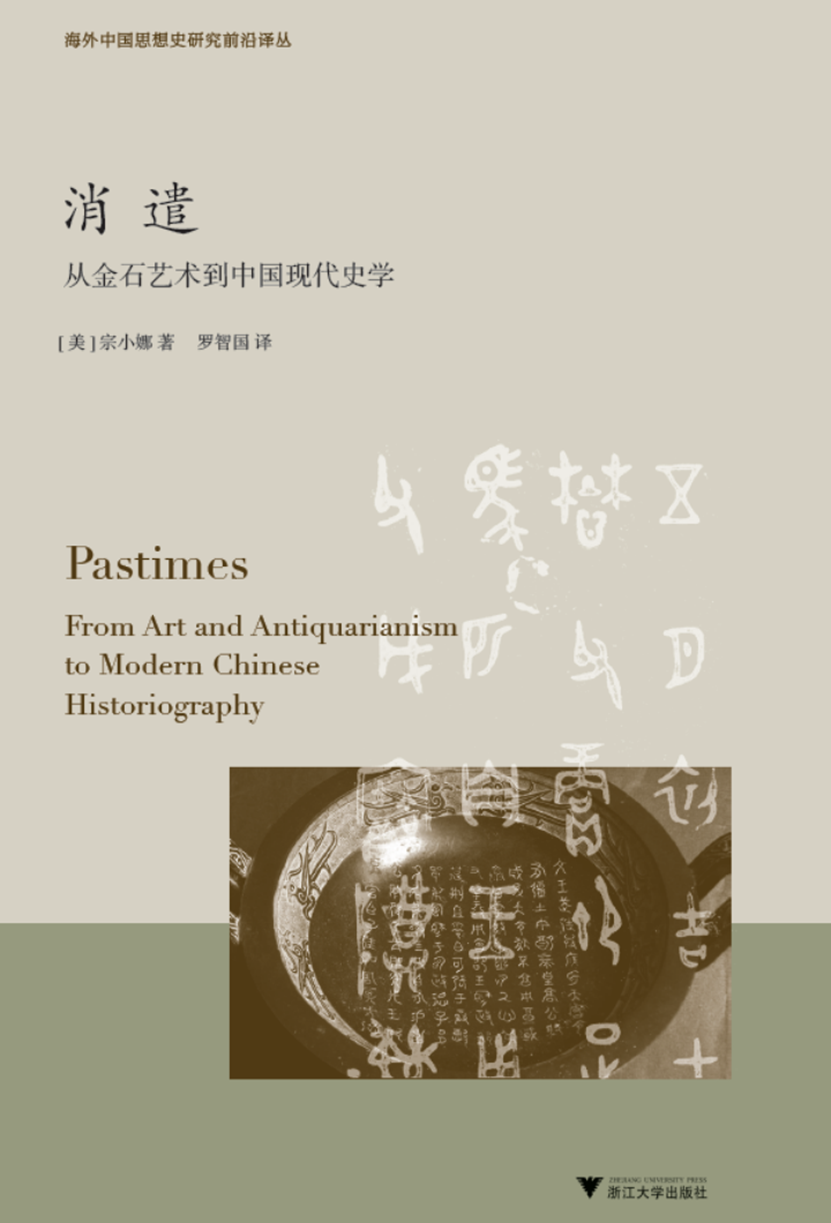
[美]宗小娜 著
罗智国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4年4月出版
内容简介:
作者通过对金石学在晚清和近代的变迁,讨论作为古代文人消遣和收藏鉴赏手段的金石学如何演变为现代历史学的一个领域。传统金石学的研究方法、思路与新的历史学方法、考古学方法相互交融,逐渐变为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新领域。由此,读者也可以窥见现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本书亦可视作一部“金石学的近现代史”,金石学在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吸收了西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逐渐演化成具有现代意识的考古学和历史研究学科。
作者简介:
Shana J. Brown
中文名:宗小娜,女,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教授。
1971年6月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县。
1993年获美国安默斯特学院东亚语文系本科学位。
2003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博士学位。
2003年开始在夏威夷大学任教。
译者简介:
罗智国,山东平度人,历史学博士。孔子文化研究院教师。学术兴趣在中国现代思想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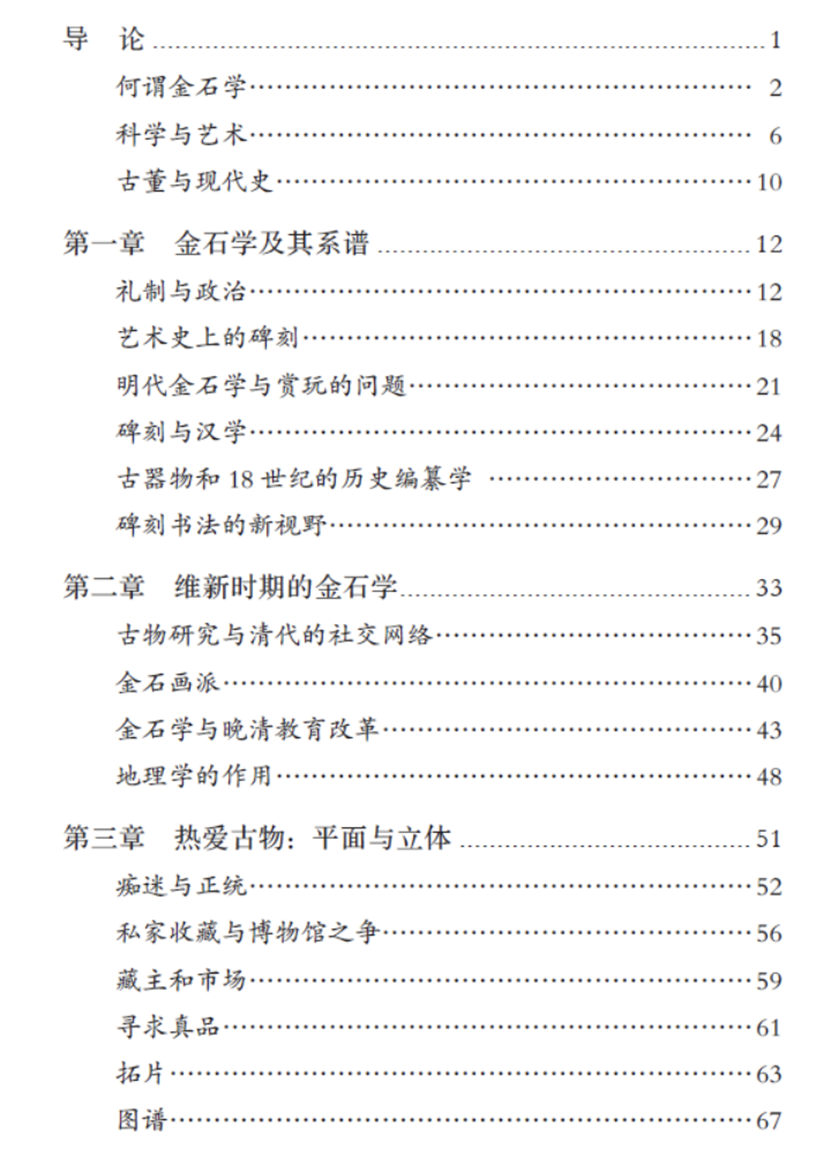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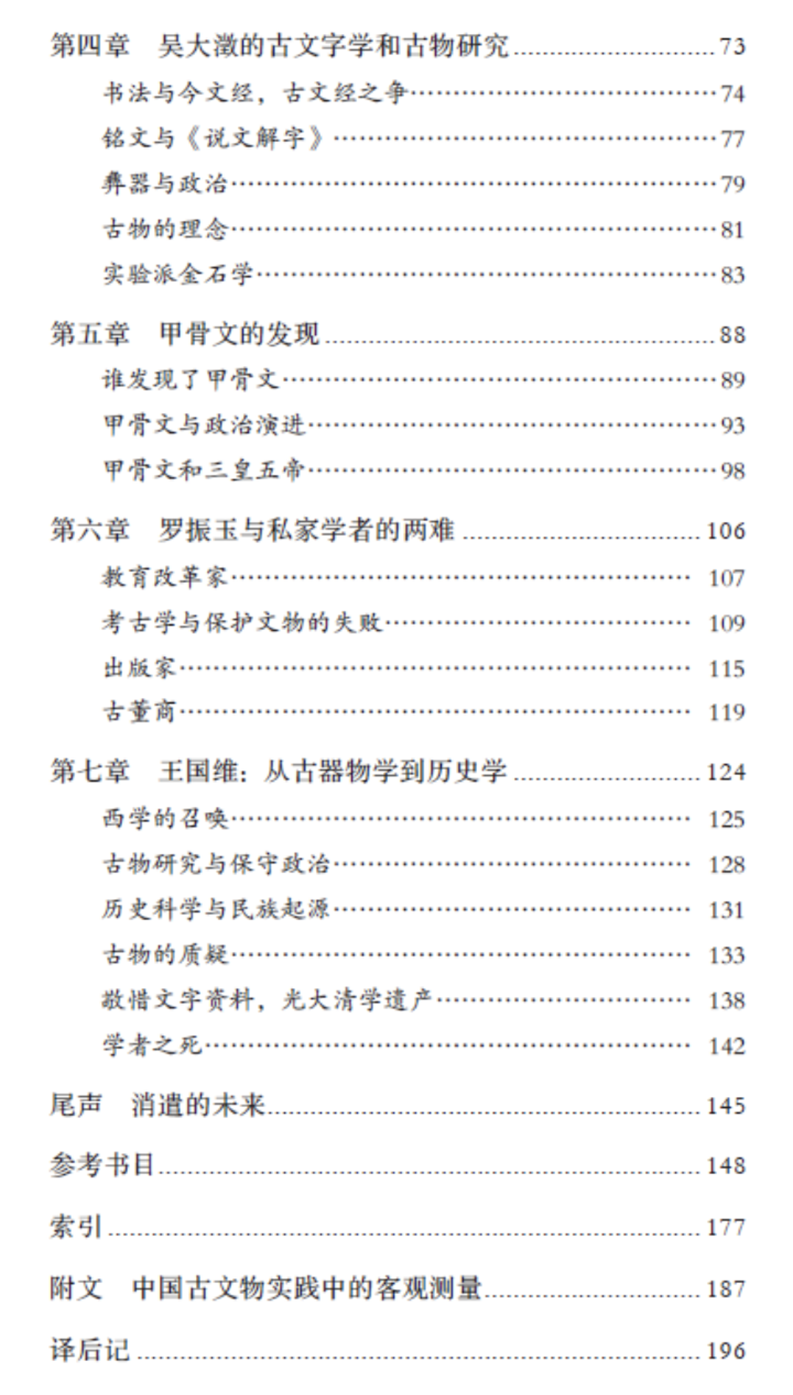
译后记
由于专业分工,艺术史在艺术院系而不在历史院系,使得史学界对艺术史相对陌生。考古学原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史学界对考古学相对熟悉,但考古学业已独立出去,成为专门的学科和院系。从艺术史的角度,追寻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的转变历程,是夏威夷大学宗小娜著作《消遣:从金石艺术到中国现代史学》的研究主题。
一般说来,学习考古学有三条途径:学习考古学方面的大学课程,学习博物馆研究的课程,在地区单位或文化资源管理部门中找份工作以获得实践经验。宗小娜选择这样一个题目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是由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经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做为期一年的志工,亲自触摸到中国古代青铜器和佛教造像等珍贵文物。她选择考古学史的题目可谓具备至少两条学习途径,所以有着身临其境的贴切感受。
中国学者做同类研究,当推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其中一节为《金石学及其向近代考古学的过渡》。“考古”二字,令人望文生义,以为中国古代就有这门学问。实际上中国古代有金石学,考古学是清末民初时期西学东渐的产物。金石学是考古学的前身,如同炼丹术是现代化学的前身、采药学是现代植物学的前身一样。陈先生归结出金石学与考古学三大根本不同:“一是闭门著书,大多研究传世和采集的金石之器,而很少与田野调查和发掘相联系;二是偏重于文字的著录和研究,对于没有文字的古代器物不感兴趣;三是与西方近代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实证方法不同,金石学偏重于孤立地研究某一个问题,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而对器物本身的形制、花纹等特征的变化、断代,由器物推论古代文化,由款识考证古代史迹等方面则多有忽略。”金石学向考古学过渡,主要从以上三个方面实现范式上的突破。顺便提及,宗小娜在注释及参考书目中都未提及陈星灿著作,以下的描述与推延,只能是该书译者兼本文笔者的揣摩与推测。译者的初衷是为读者做一点本书内容的导读。
一
传统金石学虽然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但并不缺乏出土发掘。在金石学这门学科形成之前的唐初,我们的先辈就发掘出石鼓文。大量珍稀古物发掘出土后重建天日,其中不少出自盗墓贼之手,据说盗墓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职业。虽然罗振玉1915年亲赴河南安阳小屯村购买古物,并做过详细笔记,但“甲骨四堂”除董作宾外,没有人参与过现代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法是区分金石学与考古学的方法论依据。直到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掘,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到新疆考古挖掘,1928年中研院史语所安阳殷墟发掘,现代田野调查法才得以在中国学界的专业范围内实施运用,标志着考古学正式形成。缺乏田野调查法,金石学向考古学转变还有哪些可资利用的有利条件?
这就是金石学的法宝——拓片,拓片是文物收藏和视觉文化最主要的流通物,是收藏者钟爱古玩的替代品。甲骨文学科创立者未能田野调查,但凭借拓片进行研究,依然能证经补史,进一步窥探中国上古社会之堂奥。1913年,王国维和罗振玉完成流沙坠简研究,这批简牍由斯坦因收藏、沙畹出版,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运用考古学家发掘的材料。此前1903年,刘鹗出版中国第一部甲骨文字材料的书籍《铁云藏龟》图谱,收录一千多幅甲骨拓片,第二年孙诒让根据图谱完成中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契文举例》。所以金石拓片成为现代田野调查的替代物。
制作拓片图录和购买古物、鉴赏古物并称为金石学家三大活动,在金石学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拓片作为一种视觉文化,自身也经历变迁。宗小娜著作从艺术史角度切入,发掘出此前不为人注意的史实。拓片从三个方面发生巨变:一是传统碑刻用二维平面拓片,十九世纪早期马起凤发明全形拓,青铜器等礼器开始使用三维立体拓片。立体拓片成为中国图像艺术的新起点,由此产生八破画、锦灰堆、博古画卉等新的视觉艺术形式。二是自宋代开启的金石图录,蕴含儒教的完美象征意义,青铜器在坟墓、水底或者其他高压环境中埋葬千年之久,但在图谱里看不到任何如铜绿、腐蚀、损坏等瑕疵。受西方蚀刻术和雕刻术的影响,为提高其仿真效果,古物图谱开始显露瑕疵与损伤,不再像以前那样呈现完全崭新的视觉效果。三是1890年代照相机引入中国,首先用于复制中国画,二十世纪前十年开始用来制作甲骨文照片,最终还用于拍摄彝器等古物。最早利用相片来编辑古物图谱始于容庚,他已经是受过科班训练的现代考古学家。拓片作为一种视觉文化,在诸多层面发生转变,这是金石学向考古学转变的核心要素。
金石学家对无文字的古器物本无多少兴趣,释读古文字主要依据《说文解字》。在金石学向考古学转变过程中,两个人厥功至伟——吴大澂和罗振玉。吴大澂学术生涯最早由书法艺术开端,曾耗费十年时间用篆书将《论语》抄写一遍,期间发现《说文解字》无法解释某些篆文,于是采集印在钱币、陶瓷和石鼓文上的古字,完成古文字学著作《说文古籀补》。他在视觉艺术上的贡献,是和幕僚吴昌硕一起,创立起近代书画史上的“金石画派”。吴大澂对无字古物的最大贡献,在于通过测量家藏的大量玉器,恢复上古三代的器范制度。这种物理实验法还可以理解为受到下面我们要谈到的西方科学的影响。
甲骨作为古器物,最初无人能识其文字,所以更像是无文字的古器物。王懿荣因发现甲骨文被尊为“甲骨文之父”,但有名无实,第二年即亡于庚子之乱。罗振玉总共收藏过三四万块甲骨,占全部甲骨数量的一半。他既用现代影印术出版这些甲骨图谱,又利用这些实物进行学术研究,终成“甲骨四堂”之首。他是学问家,也是古董贩子(也可译为艺术品商人),甲骨在他手里成为可以辗转获利的商品,相当一部分经手转卖他人——包括日本人。罗振玉改传统术语“金石”二字为“古器物”,由金石学而古器物学而考古学,古器物学正是金石学和考古学之间连接的桥梁。
现代自然科学的影响是金石学转向考古学的最大推动力。比如,放射性碳素断代法的发明和应用被认为是现代考古学中的一场革命。陈星灿先生研究表明,近代考古学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学科是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甚至考古学本身亦可视为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宗小娜则开掘出不为人注意的层面:视觉文化、进化论和影印术对金石学转型的影响。
首先对科学重新定义,五四以来国人一直把民主与科学作为救国救民的不二法门。科学因具有价值中立性,无人敢于撼动其至高无上的地位,政治宣传更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李约瑟大力挖掘中国本土的科学传统,但吊诡的是却引出“李约瑟难题”,总归是认为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胡适在《中国的文艺复兴》里说:“伽利略、解百勒、波耳、哈维、牛顿所用的都是自然科学的材料,是星球、球体、斜面、望远镜、显微镜、三棱镜、化学药品、天文表。而与他们同时的中国所运用的是书本、文字、文献证据。”但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从思想史意义上提出,清代朴学依然具有科学精神。宗小娜更进一步,大胆提出“十八世纪金石学真正意义,在于它是现代实验科学的先驱之一。”现代实验科学早在西学引入中国之前业已存在,吴大澂正是运用此法研究中国上古度量衡制度,所以金石学正是中国拥有本土科学传统的明证。
视觉文化是史学界未曾引起充分关注的领域。陈星灿先生在评估明代金石学成就时,只简单概括为两句话“明代理学盛行,坐而论道者众多,所以金石学呈现出倒退的趋势。……明代金石学人虽多,但多因循守旧,没有多少成绩,唯曹昭《格古要论》是有关文物鉴赏的早期著作,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这些年来,随着柯律格、高居翰、白谦慎等人的艺术史著作的翻译出版,明代艺术史研究大有改观。在明代社会的奢华风气里,《园治》《长物志》《墨志》《瓶史》等休闲娱乐之作蔚为大观。宗小娜著作发掘出明代中国的视觉文化:在书法领域里尊崇“王体”法帖而贬低“颜体”碑帖;在金石拓片图谱方面,详尽描述古物的外在特征如色调、纹路甚至味道,这些特征到严肃的清代朴学盛行时期被一删而光。在金石学向考古学转型过程中,书法领域不仅重新尊崇碑帖,甚至首次重视异族政权统治下树立起来的魏碑。而魏碑正是金石画派形成的源头之一。清代金石学家的视野大大扩展,研究对象扩展到造像、画像石、墓志、泉币、玉器、玺印、瓦当、陶俑等,金石画派书法家赵之谦做过朝鲜碑刻文字研究,傅云龙和杨守敬编印过日本碑刻图谱。所以当新的视觉艺术如甲骨图谱出现时,金石学家早已做好研究新生事物的准备。
达尔文是近代生物学的奠基人,但其学说在《物种起源》出版四十年后才传入中国,而且经由赫胥黎的介绍和严复的翻译。所以这种自然科学是以社会理论的形式影响甲午海战后有亡国灭种之虞的中国人。金石学作为旧学,没有被维新党弃如敝履,相反,清廷中的维新派大都支持和钟爱金石之学,一方面,金石本为玩物,同人之间互相借重把玩,在金石上倾注心力,为囊中羞涩的同人出资购买,为相互之间的认同感建立起亲密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金石学研究具有改善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实用价值,比如解决历史地理问题,碑文记载内容能够解决两国边界之间的领土争议。国难当头并未使维新党玩物丧志,进化论风靡一时,成为他们救国救民和学术研究的理论依据。胡适在《我的信仰》里说:“数年之间,许多的进化名词在当时报章杂志的文字上,就成了口头禅。无数的人,都采来做自己的和儿辈的名号,由是提醒他们国家与个人在生存竞争中消灭的祸害。”孙诒让用进化论的维新政治观点解读甲骨文,其开创性研究证明,金石学并非百无一用,而能为政治维新提供理论依据。罗振玉证明从甲骨文到金文的“蕃变”,是中国古文字自身的进化过程。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利用进化论的理论,将远古中国史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他们受进化论思想影响,证实中国古书记载的上古三代以及尧舜禹的真实性,驳斥了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强调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绵延不绝,在亡国灭种的阴影中提升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
新的印刷技术不仅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促进了现代学科如植物学、药学等学科的诞生。传媒文化的繁荣昌盛,使图书画片能够大量复制印刷,这最终要归功于影印石版术(photolithography)等新技术的引入,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视觉盛宴。这里用本书的一个例子和我找到的两个例子进行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
首部甲骨文研究著作是1904年刻版的孙诒让《契文举例》,流传范围不广,作为私家著作馈赠给端方、刘鹗、罗振玉等少数圈内人。王国维在上海书摊上买到一册,这一幸运发现使此书通过重版才流传下来,1927年,罗振玉的堂弟罗振常供职的蟫隐庐重印此书。
除了编印古器物图谱,据《罗雪堂合集》统计,罗振玉著述共一百七十六种,几乎全部自己印刷。罗在天津和旅顺定居时,都自办书局和印刷厂,不仅出版本人著作,还重版孙诒让、吴大澂等金石学家著作。
1928年,郭沫若到日本避难,开始研究甲骨文,两年出版三部曲《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他所用的资料即罗振玉编印的珂罗版甲骨图谱《殷墟书契前编》等,身在异国他乡,在上野图书馆、东洋文库、文求堂很容易借到这些“影印的比较珍贵的典籍”。
以上三个例子说明,影印以及后来的凸版印刷等新印刷技术的推广,完全改变了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术,把珍稀古籍化身为千万,惠及求知若渴的莘莘学子,有力推动了学术的交流与提升。
在救亡图存的清末民初历史大背景下,在西学东渐的世界大潮中,传统金石学科怎样实现现代化,转向现代考古学?我们不妨借用列文森“博物馆”命题和巫鸿“纪念碑性”的术语。列文森说“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这种历史与价值的背离可称为“博物馆化”。巫鸿对“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的定义是“指纪念碑的纪念功能及其持续,……和回忆、延续以及政治、种族或宗教义务有关,其具体内涵决定了纪念碑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意义。”如果用这一对术语来界定金石学和考古学的话,金石学才是“纪念碑性”,考古学才是“博物馆化”。考古学和博物馆归根到底是西学东渐的产物,金石学和纪念碑为中国传统文化固有之物。在东西方两种文化接榫的过程中,金石学家顽固地抵制公共博物馆(直到1920年张謇在南通建造中国首家博物馆),但金石学最终不可避免转向了考古学,纪念碑并未自动送进博物馆,它依然保存着自身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涵义。
青铜器、玉器、甲骨等古董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活化石。研究古董的金石学并非国渣,而是现代考古学的中国本土资源。在全球化大潮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都迈向现代化,但物质上越是现代化,精神上就越是怀旧。从金石学向考古学的转化过程,怀旧性地解释了学术上的移植、融合、演进与提升,整个过程纷繁复杂。金石学传统不能简单地送到博物馆仅供展览,而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纪念碑。诚如宗小娜所言,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没有什么比古董更能代表现代性。
二
关于翻译的难度问题,本书主要体现在回译方面。做学术思想史的人多有注癖,借古人之口以表达个人之意,本书需要回译的地方的确较多。大部分书籍能够依靠个人藏书和网络电子图书查阅得到,但有部分古籍却遍寻无着:一种是清末民初时期出版物,如《攀古楼彝器款识》《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善斋吉金录》等;另外一种是“出口转内销式”的汉学家译文,如倪德卫引用章学诚《文史通义》,高罗佩引用叶昌炽《语石》等。这只能求助于原作者宗小娜教授,宗教授非常谦虚称自己是合作者而非译者。作者对译者的帮助还体现在,术语表和参考书目都有中西文对照。所以在参考书目部分,如果已有中译本上市,译者尽最大可能将其附录在后。原作者引证书籍不少是台版书,鉴于大陆学者难以获取,译者还增加小注,将比较常见的大陆版本附在注释后面。原书采用尾注,本书一律改为脚注。
为助于大陆读者对宗小娜教授的了解,我把她在大陆发表的唯一一篇文字《中国古文物实践中的客观测量》译成中文,经作者同意,附录在这本书的后面。
本书主题在于论述金石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过程,如果现代史是我的专业,那么金石学就相对陌生——如果还不是一无所知的话,毕竟大学期间学历史专业时,并没有开过考古学课程,研究生阶段读近现代史专业,连古代史的书都很少触及了。其中有些拿捏不准术语,应当是本书的关键词,如青铜器、彝器、明器、礼器、吉金、钟鼎;铭文、钟鼎文、金文、籀文、古文;图谱、图录、图册、著录……每组大多为同一个英文词,但在中译本里采用哪一个,取决于前后文的连贯程度。
翻译初稿主要完成于2017年暑假,这是我在南方居住时间最长的夏季,酷热难耐,持续累月,是我这个北方人从未遇到过的。每天定时坐在写字台前,沉浸在译书的世界里,每次起身都会发现桌面上留下斑斑汗渍。翻译内容多属文人墨客之长物:青铜器、玉石、拓片、书画、甲骨等,颇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于是翻线装书、摇芭蕉扇、饮菊花茶,炎炎酷暑是知识分子的神仙岁月。闲暇即工作,工作即闲暇,后者的境界我还达不到,在暑假这段闲暇时间里做翻译工作,使我觉得时间没有被浮生蹉跎。
趁着短暂地暑假回乡的机会,到曲阜三孔和嘉祥武梁祠一游。本书提及古文经书的发现地“孔壁遗书”(Walls of Confucius’s family home)原在孔庙而不在孔府。虽然早年进出三孔多次,但这次总会牢牢记住。“武梁祠”是巫鸿的博士论文及成名作,但并非正式地名,在地图上查不到,应为“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是汉代武氏家族的墓群,出仕者有武梁,武梁弟弟武开明,武开明长子武班,次子武荣。此等虽为细枝末节,却为翻译工作平添更多乐趣。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很多友人的帮助,其中有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秦素银,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刘允东,河南师范大学的张文瀚,四川师范大学的刘双怡,曲阜师范大学的陈洪友,安徽师范大学的赵娜和任立侠,山东嘉祥县文物局楚桂花,作为该领域里的专家,帮我解决翻译中涉及到的不少专业问题。特别感谢中华书局的潘鸣,如果没有他的大力推荐和穿针引线,我就拿不到这次翻译的机会,使我翻译的第二本书终于能够首次出版面世。最后但非最末,向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伏建强等编辑致谢,如果没有他们的妙手仁心,就无法向读者展示这样一间凤冠霞帔的嫁衣。
2018年夏初稿于长江之畔
2024年春定稿于黄海之滨


